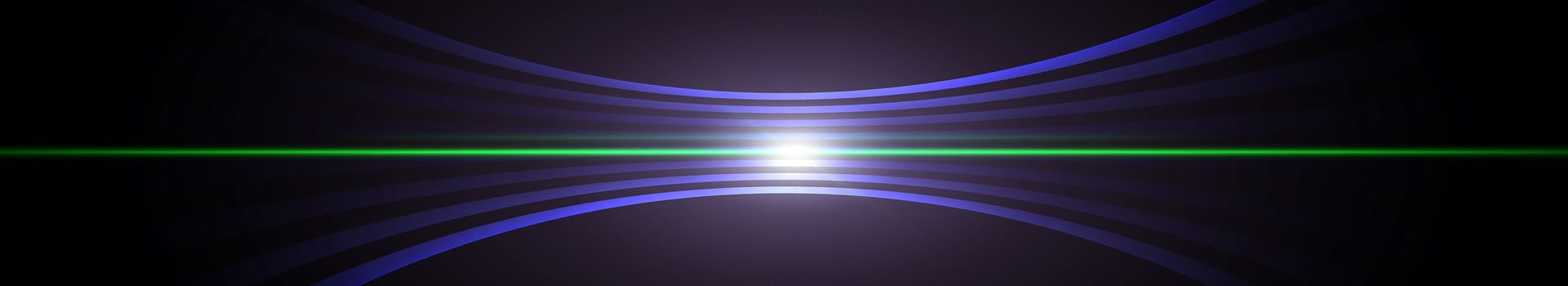

九大召开前夕,原本是计划由我、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负责起草报告稿件。然而,我并不愿意与张、姚等人协作。因此,我将自己的名字置于起草人名单首位,随即开始着手工作,并召集了几位同仁协助搜集资料,同时亦亲自撰写了一部分内容。记得在完成稿件的部分章节后,我便先行将这部分内容送审。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此处疑有不清字)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
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即一切,而目的却无处可寻。’”
张春桥立即对我的开场白提出反驳:“你所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此处补充了我先前所述内容中遗漏的张春桥所言,以补全原意。)
毛主席听闻我的言辞后,步入卫生间稍作沉思,归来时便提出:“我考虑在报告之中纳入陈伯达的建议。”
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与我进行了意见交流,尽管当时在会议中他选择了沉默,然而,他明确拒绝了张春桥的错误观点。
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为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无论康生及其“四人帮”是否自诩为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声誉早已一落千丈,他们必然抓住机会对我提出此类比拟进行反击。而这场反击,自然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爱因斯坦”的称号问题。
周恩来同志曾向我透露了关于九大选举常委的情况。他惊讶地对我说:“我未曾料想你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之中。江青曾公开发言,若黄永胜能成为常委,她亦不甘落后。有位同志因此提议,常委名单无需变动。”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稿子。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均需毛主席亲自审批。”毛主席接过文件后,立刻划去了“江青同志”四个字。
总的来说,她在北京的生活并不顺心。在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同短暂返回上海期间,他们讨论了九大之后的各种策略。为何他们不留在北京?那是因为中央会议和中央事务仍由周恩来同志掌舵,他们的阴谋遭遇了阻挠。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注:称)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以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套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于庐山之巅,正值会议尚未揭幕之际,周恩来同志曾途径我居所,与我谈及江青同志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我回应道:江青同志对毛主席并无忠贞之志,她曾不止一次向我透露,她意图离开毛主席。首次,是在延安的枣园,她曾表示,欲离毛主席而去,并寻两人负责照料他的起居。第二次,在西柏坡,我前往探望毛主席时,恰逢他不在,江青同志再次提及,她打算离开毛主席,前往他处。第三次,在解放后的北京西山,我拜访毛主席时,他亦不在,江青同志又一次表达了她欲离开毛主席的意愿。
周总理听闻我提及北京西山之事,便紧接着表示:“关于西山的情况,我有所了解,那是毛主席指示我需将她送往莫斯科。我认为,江青提及的欲离毛主席的三次,均发生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即便北京已解放,战事仍在进行,事务繁杂,她却以个人之事干扰毛主席,声称这是‘忠于毛主席’,岂非太过荒谬?周总理排除她的干扰,将她送往莫斯科,此举实为明智之举。”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特别是在九大后,林彪和江青在夺权问题上竞走。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与江青均在暗中积极布局,意图夺取权力。至于他们具体采取了哪些行动,我并非完全了解。曾有一段时间,我向毛主席请示,希望能够前往华北各地进行考察,毛主席对此表示了同意。随后,我将此事告知了周恩来同志,并告知了他我将采取的路线,周恩来同志也对我的出行计划表示了赞同。
关于此事,康生及四人帮后来竟将其视作我的一大罪状。实则,我在遵守纪律方面并无过失。经过几地的辗转之后,我重返北京,向毛主席及中央提交了一份简要的报告,其中并无任何阴谋。
在华北数地,文革时期,毛主席与周总理曾命我关注相关事宜。随后,我前往青春之地,同时,亦严格审视自身,检视自身言行中的不当之处。就纪律而言,此举亦属正当。然而,康生及四人帮不仅对我罪加一等,更无端地将我牵连,导致一些优秀的同志遭受了不必要的苦难。
九大召开之后,康生负责对宪法进行修订,并邀请我参与其中。依我记忆所存,康生最初拟定的序言中,并未提及人民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建设,仿佛中国的革命仅在“文革”初期才真正起步。尽管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有所增补,但并未赋予这些内容应有的分量。
怀仁堂内召开了这场讨论会。在一日夜晚,我身处卫生间之际,突然听到了吴法宪声音洪亮,似乎还伴有拍桌子的响动。当我步出卫生间,场面已然归于平静,会议也随之结束。
吴法宪依旧留步,我好奇地询问起他们争执的具体缘由。吴法宪透露,争执的焦点在于张春桥对“毛主席是‘天才’”这一论断的否认,正是这一观点引起了他的激烈反应。
听闻吴法宪所言,我深以为然,因为我也认同毛主席乃一位非凡的天才。即便在往昔,我未曾如此直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曾认可历史上存在天才人物,将毛主席誉为“天才”并无不妥。
在与吴法宪的交谈中,我并未对此事过度渲染,而只是听闻他的说法后,觉得张春桥的行为颇显荒谬。交谈迅速结束,我便与吴法宪一同离开了怀仁堂。会议室内的人员早已散去,然而,我注意到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独自一人留在汽车中未曾离开,我想,他或许是康生特意留下以便观察的人。
我未曾预料到,怀仁堂的那次发言,在庐山会议中竟演变成一场灾难。所谓的“大有摧毁庐山、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我想,这大概是康生和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及吴法宪在怀仁堂时的激烈言辞和拍桌行为。由于吴法宪曾是“空军司令”,他们可能认为他有能力“炸平庐山”。然而,我自身并无此类能力,既无能力也无手段,又怎能做到炸平什么呢?

林彪和陈伯达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幕前夕,林彪同志独辟蹊径,与毛主席在私密空间进行了单独交谈。周恩来同志以及我等其他人则移步至另一房间,耐心等候,期间虽不算漫长。毛主席与林彪的私密会面结束后,大会随即拉开序幕。原本安排康生同志作“宪法草案”的报告,但林彪同志却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回忆,他的发言主要围绕宪法草案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其天才理论的阐述。
林彪发言完毕后,康生随即向我发起挑战,要求我先发表见解。我并未立即回应。随后,康生便穿插着发表了若干言论,其间亦不时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言辞。
散会之际,我心中不禁生疑,欲询问林彪其发言是否已获毛主席首肯。林彪回应道,毛主席早已得知他的讲话内容。
自林彪的住所步出,便来到了“军委办事组”几位同仁的居所。我顺道探访,他们便询问我是否能够寻觅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言论。我应允了此事。
我承接此任务,实属冒失之举,因在攀登途中,我并未有意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当时,我只随身携带了《列宁选集》,至于是否还带了其他书籍,已记不清。于是,在山上临时委托同行者为我搜寻资料。当晚,我通过电话将搜集到的信息逐条告知吴法宪,并另行誊写一份,次日会议时呈交给了汪东兴。
我隶属华北小组。在会议中,我的发言不仅被会议记录所收录,我还事先草拟了几句简短的文字,尽管具体内容已无法详述,但天才这一话题的确是有所提及的。
华北小组的简报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据我所忆,其中似乎含有“揪出某人”之类的措辞。依我之见,此类语句并非出自我之口,亦非李雪峰同志或华北其他同志的言语。若我的记忆尚可信赖,那么这句话应当是汪东兴同志所言。
某日,林彪召集了一众人士共聚一堂(据我推测,此举系应毛主席之命),与会者包括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及汪东兴与我。在会议中,林彪与汪东兴对我提及了二十年前的一些离奇往事。随后,在全体会议上,这些问题亦被再度提出,被视为重大议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便召唤我一同前往莫斯科。在那里的谈判过程颇为缓慢,我因久未见到第一个孩子(他已故去,当时正在苏联深造)而心生挂念,便将他接到我国大使馆暂住,同时我也前往陪伴他住了两天。然而,这一行为竟成了我的疑虑所在。当时我国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而大使馆亦系我国自有的,并无外来人员出入;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这简单的举动会被视为一种嫌疑。
在全会或是各小组的会议中——无论场合如何,我均未能出席——有人特地提及了我参观“罂粟花”的经历,因此我不得不对此事进行一番说明。记得某晚,苏联的联络员费德林(精通汉语)邀请我一同观赏芭蕾舞剧。
尽管我曾在苏联求学,却未曾目睹过此类剧种。承蒙主人盛情,我便向毛主席提及此事,于是便前往观看。时至今日,岁月已过数十年,我年事已高,记忆日渐模糊,但依稀记得:那剧本讲述的是中国革命的故事,然而剧情却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大相径庭。因此,在剧场中,我始终感到困惑,未曾鼓掌。费德林多次劝我鼓掌,但我仍旧没有动。直至剧终,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尤其是他们对我国客人的热情款待,以及对中苏友谊的颂扬,以及对观众盛情的感激,我也终于向观众鼓起了掌。
剧终之际,剧场指挥主动与我交谈,征询我的观感。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参与中国革命的一员,我认为剧情与现实相去甚远。此次观剧经历,让我感到不快,最终带着遗憾离去。返至住处,我将此事及个人观点向毛主席汇报。观看《红罂粟花》的全过程亦如此。得知庐山会议对此事有所讨论,并认为我观看此剧有罪,这让我陷入了沉默,不知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这一次我被要求观赏这部剧,但在此之前,我先行探询了国人的观感,这作为一种为毛主席观赏所做的初步准备。后来,苏联方面亦欲邀请主席观看,然而毛主席已从我这了解到剧情,因此便没有前往。
在这场庐山会议上,那桩微不足道的小事竟演变成了我背负的罪孽。
事情的经过和我的了解,我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怪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现在你有什么想参观的地方,尽管去看。”回想起那次参观,我不仅观看了列宁的集体农庄,还探访了列宁晚年休养及离世之地,并遵照引路人的要求,记录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感。在参观前,我已向毛主席请示过,并在事后向他做了汇报。
鉴于所谈内容与庐山会议议题密切相关,故此阐述上述观点。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江青与张春桥在阅读《华北组简报》后,起初显得有些不安,毕竟他们素来擅长“揪人”,如今却有人试图将他们置于同样的境地。彼时,正值“揪人”风潮正盛,我向康生提及,自己先前对“揪”与“砸”这两个字并不熟悉,《康熙字典》中亦未收录。康生随即从《康熙字典》中检索出这两个字,以证我之无知。然而,如今“揪”字却似乎要被加之于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这不正应了中国那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古训吗?
我推测,若有人提出“揪出来”的建议,他们应当能够得知。郭玉峰参与了华北组的活动,他频繁出入康生与曹轶欧的交际圈,而康生与曹轶欧又与江、张等人交往甚密,或许消息正是从郭玉峰那里传出的。
于毛主席召开会议之际,我依稀记得江、张二人并未现身。原来,他们早已向毛主席申诉,似乎已然赢得胜利,故无需再出席。而我与李雪峰虽出席会议,却仿佛沦为被告。至于那位倡议“揪出来”的同志,他当时是否与会,我已无法确切回忆。自此之后,我便未曾再出席毛主席主持的会议。
在事件的演变途中,我曾拜访过周恩来同志。他回忆道:“江青与张春桥是率先向我提出谈话要求的,然而在我们尚未晤面之际,他们便匆匆离去,径直前往毛主席处。”
在那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近两年来,你为何未曾前来拜访我?”
毛主席的这句话,对我而言,承载着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往。确实,在过去的两年里,除了参加各类会议,我鲜少有机会单独觐见毛主席,这已违背了往日多年的惯例。解放初期,我最初居住在党校,后来毛主席希望我参与一些工作,便让我搬至中南海居住。毕竟,从党校打电话召见我,至少需要半个钟头,极为不便。而搬至中南海后,见面则变得异常便捷,我总能随时应召。然而,“文革”时期,江青对我与毛主席的会面进行了干预,她认为我每次交谈的时间过长。不久之后,恰逢刘淑晏(陈伯达夫人——编者按)未征得我的同意,我便再次入住钓鱼台。她未经我同意,便擅自通过公安部在我住所进行了一次错误的调查(查寻一个脚印,原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若我事先得知,我想我不会同意这样做)。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了此事,江青随即对我下达了逐客令,“中南海乃主席的居所,你们不得再在此居住,必须搬离。”
由于藏书众多,且有时希望与同志们共同行事更为便捷,我便恳请北京市委的负责同志协助寻找一处居所。最终,选址新建胡同。然而,江青下令将我逐出中南海,于是我们全家便搬迁至新建胡同安顿下来。
自那之后,若欲拜访毛主席,便需先通过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询问,诸如主席是否起床、是否已有宾客来访等。其间,不乏几次询问时的不快经历,甚至有次秘书直接回应:“我要回家了。”因此,我逐渐意识到,想要见到毛主席并非易事,于是便减少了单独求见主席的次数。这类事情首先便涉及江青,向毛主席说明此事,我感到颇为棘手。诚然,对党组织而言,这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毛主席在见面时便直接提及“两年未见”的问题,这充分显现了江青挑拨离间手段的影响力。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前往拜访江青。抵达庐山之后,江青先后两次来电,邀我至其住所,我却未曾赴约;此后,她又有电话告知将亲自前来,但她终究未曾成行。因此,我们一直未能见面。这次当我抵达她的住处时,她不禁连声呼喊:“稀客,稀客!”未曾多言,便催促我随她一同前往康生的住所。
步入康生的住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曹轶欧,但她并未主动搭话。踏入康生所居住的宽敞宅邸,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场,这表明他们频繁聚首商讨事务。交谈随即展开,我犹记得江青开口便说:“你们口口声声称颂林副主席,实则内心却在抵制……”随后的发言中,众人纷纷激烈争论,但具体的言辞已无法悉数回忆。
不久之后,组织方面传来消息,周恩来同志与康生同志将协助我完成反省材料的撰写。
周恩来同志向来话语不多,是康生同志在会上发言。至于我在庐山所作的检讨,其内容大体上遵循了康生的指导。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回答:“无需羞涩”。
在检讨会的次日,我心中原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思及回家投身农业,内心不禁松了一口气。然而,转念间,我又觉得事情并未如我所想那般简单。或许是恩来同志对我仍有所牵挂,特意安排了医生和护士前来看望。我打算前往庐山一游,便邀请他们以及负责接待的同志一同前往。在欣赏到美景之际,我们一同合影留念。拍照之后,我们继续游览山水。这一天,无疑是自抵达庐山以来我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风声四起,悲情便随之涌上心头。流言四散,如此传开:“陈伯达并未流露哀痛之情,反而悠然游山玩水。”会议再次召开。那时,我已无法参与任何大小会议,但简报似乎仍能一睹为快。有关我的诸多事宜,都是通过简报得悉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所谓在重大问题上缺乏配合,并非意味着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均未予以配合”,并随即列举了具体事例以佐证。
在那个特殊时期,周恩来同志竟然如此坚定地维护我,这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他对事对人秉持的公正态度。
返回北京后,我多次想要恳请毛主席以及中央予以谅解。入夜,我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希望能面见其一面。不久,毛主席的秘书回拨了电话,告知毛主席刚刚结束会议,身心疲惫。自然,我也就不便再提相见之事。
拨通康生的电话,却被告知他未能接听。即便转而请求曹轶欧接听,她同样没有应答。
然而,在拨通周恩来同志的电话后,他的秘书请我稍作等候。不久,周恩来同志亲自接听了电话。他那温和的语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恩来同志从不因个人犯有过错或遭遇困境而轻率地予以摒弃,而是选择给予他们希望。我认为,这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所体现的精神。
返京之后,我于数个夜晚踏足郊野,漫步其中,以舒缓内心的烦闷。不久,接到通知,要求我停止外出。国庆佳节将至,担心我会偶遇外籍人士。

自此,我深居简出,足不出户。协助我管理文件的两位同事被调往学习班,据说这是为了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预感到了逮捕的可能。在这绝望的时刻,我向那位同时负责药物管理的同事提出请求,希望他在逮捕发生时,能设法为我提供一些安眠药。然而,他担心因此引发麻烦,最终将药品退还给了医务所。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过:“在阜平,我确实曾行善积德。”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数日之后,或许是我于监狱门前所吐露的那番话语已有所上报,于是我被转移至三楼之上(整层楼仅我一人被囚禁),随之陷入沉睡。
生活备受厚爱,每日都有医生悉心照料,饮食精致,甚至胜过家中。我得以安享今日之生,衷心感激秦城管理团队的辛勤付出。当然,他们是在贯彻党的指示,对此我充满感激,感谢党的关怀,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英明领导。
我思忖:只要生命犹存,疑问终能得以厘清。于是,内心逐渐恢复平静,自杀的念头也随之消散。
我心中永远怀有对毛主席的深深感念。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他给予我深刻的教诲,使我得以粗略地领悟到中国革命的些许真理。毛主席还为我提供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诸多便利。纵然我学识浅薄,屡犯错误,即便偶尔有所著述,也常是谬误百出,经不起严苛的审视,这只能反映出我的不足。我深切地体会到求知之不易。学生不成才,并非全然是老师的过错。
我必须承认,毛主席是一位卓越的天才。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贡献堪称空前绝后。诚然,历史上每一位天才人物,即便是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亦难以完全避免某些瑕疵或失误。稍作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便能略窥一二此类问题的端倪。
此外,我们亦不可仅因某人过去未曾认同马克思主义,便断定其出生时已被注定,从而断言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将其永远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并未持有此种观点。
试举梅林为例。梅林本来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同他通的信,对他表现了很大热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曾经对梅林这样称许过:“梅林不仅是一位渴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更是一位擅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高手。”
康生与四人帮自诩为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自己始终正确无误。在他们看来,若有人与他们观点相左,便是犯下弥天大罪,其恶行将影响子孙三代。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在庐山会议前后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除了林彪的罪行之外,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亦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与外界交流常受阻碍。
我自感才疏学浅,即便有幸时常见到毛主席,亦难以有所贡献。关键在于,毛主席与广大同志的交流已遭受江青等人所造成的干扰,因此在处理事务时难免出现不足,甚至犯错。即便毛主席如此伟大英明,在晚年遭遇此类挫折,也让人对四人帮充满愤慨。至于“文革”期间所犯的任何罪行,只要与我之职责相关,我均将自行承担,绝不将罪责推诿他人,更不敢对毛主席有所推卸,否则我罪孽将更加深重。


